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出土于青海省乌兰县(wūlánxiàn)泉沟一号墓的王冠修复后重现光彩。
出土于青海省乌兰县(wūlánxiàn)泉沟一号墓的王冠修复后重现光彩。
 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方舱内,考古人员(rényuán)和文保人员正在开展工作(gōngzuò)。
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方舱内,考古人员(rényuán)和文保人员正在开展工作(gōngzuò)。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yánjiūyuán)刘念在实验室开展工作。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国历史研究院(yánjiūyuàn)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yánjiūyuán)刘念在实验室开展工作。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国历史研究院(yánjiūyuàn)提供)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大成果发布会现场展示的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tángdài)陶质龙首修复实物。
新华社记者(jìzhě) 李 贺摄
如何让出土王冠的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guīwèi)?如何将碎成上百块的龙首拼接(pīnjiē)起来?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如何应用到中亚考古现场……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jīng)发布(fābù)7项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上万次精密焊接(hànjiē),王冠重现光彩
在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一顶珍珠(zhēnzhū)冕旒龙凤狮纹嵌宝石王冠静静陈列于恒温展柜中。冠体上翼龙昂首、立凤(lìfèng)振翅、双狮护佑,珍珠冕旒如星垂落。从王冠造型上看,龙纹、冕旒源自中原(zhōngyuán)文化,立凤、双狮造型带有中亚(zhōngyà)风格,印证了青海“高原丝路枢纽”的文明交流融合特质(tèzhì)。
时间回到2018年。从这一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青海省乌兰县泉沟一号墓进行(jìnxíng)发掘(fājué)。2019年,联合考古队经过严谨缜密(zhěnmì)的(de)考古发掘工作,在(zài)该墓的墓室内发现了隐藏的暗格,暗格中出土了一顶吐蕃时期王冠。
历经千年(qiānnián)岁月,王冠(wángguān)在出土时几乎“支离破碎”,整体发生了严重的腐蚀劣化。“王冠的金属胎体脆弱到了极点,厚度不足200微米,差不多就是3张(zhāng)A4纸那么薄,轻轻一碰就会断裂;王冠前方垂坠的冕旒宝石(bǎoshí)串珠形制(xíngzhì)湮灭,原本的样子完全无法辨识,纺织品(fǎngzhīpǐn)内衬也整体严重损坏(sǔnhuài),文物已经完全丧失结构稳定性,存在严重的保存风险,可以说,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技术难度直接‘拉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负责人黄希如是介绍王冠出土时的样子。
由于长期埋藏,王冠额前垂坠的(de)珍珠冕旒串珠已散落如沙,黄希所在(suǒzài)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借助X光透射成像、平板CT等无损技术手段对冕旒进行分析,并在室内清理过程中识别保留原始(yuánshǐ)结构的局部单元,明确记录每一颗(yīkē)珠饰(zhūshì)的排列顺序(shùnxù)与连接关系,最终将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这是目前通过科学发掘、保护修复,准确复原的编串结构最为复杂、单体珠饰数量最多的古代礼仪性珠串组合。
“经过上万次的精密(jīngmì)焊接,王冠和冕旒的形制与精美纹饰得到恢复,高原丝路文明之冠再次焕发出千年前的灿烂光彩。”黄希说(huángxīshuō)。
回看此次修复,文物保护修复团队面对的(de)是(shì)“多(duō)材质、高(gāo)脆弱、强腐蚀”三重难题。面对难题,团队借鉴了“考古地层学”理念,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通过文物清理与保护性拆解,对王冠各部件本体结构、叠压组合(zǔhé)关系等进行准确分析(fēnxī)和记录;在文物病害和腐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材料(cáiliào)和修复方法的研究,比如创新研发出(chū)针对金银合金、鎏金质文物的专用补配修复方法。“结合前两步工作,对王冠的多材质构件连接组合关系进行复原研究,开启了一场精密的‘文物手术’,最终恢复王冠原貌。”黄希说。
还原唐代(tángdài)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发布现场,两个出土于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18号建筑(jiànzhù)址的唐代陶质龙首陈列于展柜中,引来不少与会嘉宾(jiābīn)的关注。其中(qízhōng)一件头顶正中生出一根独角,独角上(shàng)还带有6个螺旋“小犄角”,既灵动又勇猛。而在去年10月28日刚出土时,它们还是上百块碎块(suìkuài)。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唐代的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考古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wánzhěng)。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相对较完整(jiàowánzhěng)的唐代陶质龙首十分罕见。
去年11月3日,出土龙首被(bèi)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验室考古方舱。如何拼接是刘勇和其他(qítā)课题组成员面临的一大挑战。
他们首先用科技手段为两个龙首做了“全面体检(tǐjiǎn)”,了解了其制作流程——龙首是使用较纯的高硅黏土,添加秸秆等有机羼和料及(liàojí)碎陶块,先塑龙首上颌和鼻子,以此为支撑再塑眼睛及额头部位(bùwèi),再经高温烧制成型。表面大面积使用含铅(hánqiān)白色颜料进行绘制,眼珠用含锰的紫黑色颜料绘制,眼线使用含铜(hántóng)的绿色(lǜsè)矿物(kuàngwù)绘制,眼珠和眉部交接处使用朱砂进行绘制。这说明,唐代工匠在制陶、彩绘工艺、雕塑技艺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刘勇介绍,为了让(ràng)千年龙首重焕光彩,在龙首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课题组采用(cǎiyòng)了室内清理(qīnglǐ)、多视角三维成像、遗存提取、超声波清洗、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三维激光扫描、虚拟(xūnǐ)拼接、实物拼接、补配等技术,成功修复了2个龙首,还原了唐代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研究表明,9号龙首应为垂兽,10号龙首应为戗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de)建筑垂脊(chuíjí)(jí)宽度(kuāndù)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kěyǐ)想象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龙首雄浑有力、勇猛威严,为中国古代龙形象增添了新(xīn)类别,为研究唐代龙首建筑构件提供了重要材料,为龙文化形象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也进一步实证了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脉传承。
展示精细化(jīngxìhuà)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
帕米尔高原(pàmǐěrgāoyuán)西侧的费尔干纳盆地地处(dìchǔ)古丝绸之路要道,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2024年,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该盆地的蒙扎铁佩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le)新的突破。
遗址(yízhǐ)中有多人合葬墓,由于被水冲刷,上层遗物(yíwù)堆积散乱,文物质地脆弱,为遗存辨识和文物保护(wénwùbǎohù)带来困难。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shíyànshì)下设的“一带一路”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成员奔赴蒙扎(méngzhā)铁佩遗址,开启了文保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综合保护实验室)负责人韩化蕊是成员之一。
“我们先在乌方协助下搭建起了(le)临时方舱,但方舱无法满足(mǎnzú)工作条件,就把北京的(de)实验室‘拆解重组’,精选了便携设备,必要的材料,搭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韩化蕊说。
在(zài)韩化蕊看来,他们是将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wénwù)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应用到了中亚考古现场。比如,联合(liánhé)考古队中方队员采用整体套箱技术,将这些脆弱遗存完整封装,既最大程度减少移动(yídòng)对文物的(de)损害,又为后续的精细化研究保留了原始堆积信息,真正实践了“发掘即保护”的学术理念。
对出土金属器的(de)处理是蒙扎铁佩遗址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文保工作团队的做法(zuòfǎ)是对脆弱(cuìruò)的器物进行现场清理加固,提取后又通过除锈(chúxiù)处理让大量耳环、坠饰等文物重现光彩。其中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一枚五铢钱,经过保护处理后,钱币上“五铢”两个字清晰可辨。这也是此次发现的最直接的古代东西方交流证据。更特别的是,这枚铜钱是墓主人佩戴的装饰品,已经超越了货币流通的价值,生动展现(zhǎnxiàn)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chuánbō)与(yǔ)影响。
此外,在此次文保团队中主要负责纺织品保护的(de)纺织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大玮通过及时用丝网加固(jiāgù)保护,结合出土位置和遗存形制判断,还发现了(le)大量服装结构部件。绢、锦、缣、布等(bùděng)多种纺织品的出土,尤其是织锦的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品传播和纺织技术(jìshù)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韩化蕊表示,在综合了多学科研究工作(gōngzuò)的基础上,本次现场文保工作为(wèi)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新的佐证(zuǒzhèng),同时也向乌方展示了中国的精细化考古发掘和现场文保协同理念及(jí)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蜻蜓眼式玻璃珠印证“前(qián)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小小的(xiǎoxiǎode)玻璃珠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点实验室助理(zhùlǐ)研究员刘念关于中国早期玻璃珠饰溯源的一项研究成果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据刘念介绍,泡碱(pàojiǎn)玻璃(bōlí)是一种以天然泡碱为助熔剂原料的钠钙玻璃,它最早(zuìzǎo)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随后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地区。这种精美的珠饰,不仅是装饰品(zhuāngshìpǐn),更是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硬通货”。
在中国,泡碱玻璃集中发现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湖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其中以蜻蜓(qīngtíng)眼珠为主要形制,兼有少量单色(dānsè)珠。
这些玻璃(bōlí)从何而来?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发现的早期泡碱玻璃应产自地中海东岸,对于其进入中原地区的传播(chuánbō)路线,学界目前认知模糊。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出土的泡碱玻璃可能经由(jīngyóu)欧亚草原(cǎoyuán)直接输入,但这一观点缺乏系统性证据支持。
现有考古证据表明,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疆(xīnjiāng)地区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重地。自公元前一千纪以来,伴随游牧文化的(de)兴起与扩散,该地区人群活动范围显著扩大,区域间文化互动不断深入。那么,来自地中海的泡碱玻璃是否可能经由新疆传入中原呢?虽然前人(qiánrén)已(yǐ)对新疆出土的单件泡碱玻璃开展过个案分析,但(dàn)泡碱玻璃在新疆的整体分布(fēnbù)特征、工艺属性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仍存明显缺环,这导致泡碱玻璃东传(dōngchuán)的完整链条始终未能清晰构建。
刘念的研究针对的正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4处遗址出土的25件蜻蜓(qīngtíng)眼式玻璃珠,采用主、微量成分分析与显微CT技术,揭示其源头(yuántóu)与传播(chuánb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珠源自黎凡特初级生产中心,其与甘肃马家(mǎjiā)塬(yuán)战国墓样本的成分和器形基本一致,实证泡碱玻璃经新疆—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西北路径。
“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以科技证据链(liàn)进一步印证了‘前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的存在,为早期亚欧文明互动提供新的关键实证。”刘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重大成果包括重要文物修复成果、“一带一路”中外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成果、重要研究阐释(chǎnshì)成果3大类共7项。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hǎiwàibǎn)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大成果发布会现场展示的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tángdài)陶质龙首修复实物。
新华社记者(jìzhě) 李 贺摄
如何让出土王冠的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guīwèi)?如何将碎成上百块的龙首拼接(pīnjiē)起来?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如何应用到中亚考古现场……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jīng)发布(fābù)7项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上万次精密焊接(hànjiē),王冠重现光彩
在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一顶珍珠(zhēnzhū)冕旒龙凤狮纹嵌宝石王冠静静陈列于恒温展柜中。冠体上翼龙昂首、立凤(lìfèng)振翅、双狮护佑,珍珠冕旒如星垂落。从王冠造型上看,龙纹、冕旒源自中原(zhōngyuán)文化,立凤、双狮造型带有中亚(zhōngyà)风格,印证了青海“高原丝路枢纽”的文明交流融合特质(tèzhì)。
时间回到2018年。从这一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青海省乌兰县泉沟一号墓进行(jìnxíng)发掘(fājué)。2019年,联合考古队经过严谨缜密(zhěnmì)的(de)考古发掘工作,在(zài)该墓的墓室内发现了隐藏的暗格,暗格中出土了一顶吐蕃时期王冠。
历经千年(qiānnián)岁月,王冠(wángguān)在出土时几乎“支离破碎”,整体发生了严重的腐蚀劣化。“王冠的金属胎体脆弱到了极点,厚度不足200微米,差不多就是3张(zhāng)A4纸那么薄,轻轻一碰就会断裂;王冠前方垂坠的冕旒宝石(bǎoshí)串珠形制(xíngzhì)湮灭,原本的样子完全无法辨识,纺织品(fǎngzhīpǐn)内衬也整体严重损坏(sǔnhuài),文物已经完全丧失结构稳定性,存在严重的保存风险,可以说,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技术难度直接‘拉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负责人黄希如是介绍王冠出土时的样子。
由于长期埋藏,王冠额前垂坠的(de)珍珠冕旒串珠已散落如沙,黄希所在(suǒzài)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借助X光透射成像、平板CT等无损技术手段对冕旒进行分析,并在室内清理过程中识别保留原始(yuánshǐ)结构的局部单元,明确记录每一颗(yīkē)珠饰(zhūshì)的排列顺序(shùnxù)与连接关系,最终将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这是目前通过科学发掘、保护修复,准确复原的编串结构最为复杂、单体珠饰数量最多的古代礼仪性珠串组合。
“经过上万次的精密(jīngmì)焊接,王冠和冕旒的形制与精美纹饰得到恢复,高原丝路文明之冠再次焕发出千年前的灿烂光彩。”黄希说(huángxīshuō)。
回看此次修复,文物保护修复团队面对的(de)是(shì)“多(duō)材质、高(gāo)脆弱、强腐蚀”三重难题。面对难题,团队借鉴了“考古地层学”理念,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通过文物清理与保护性拆解,对王冠各部件本体结构、叠压组合(zǔhé)关系等进行准确分析(fēnxī)和记录;在文物病害和腐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材料(cáiliào)和修复方法的研究,比如创新研发出(chū)针对金银合金、鎏金质文物的专用补配修复方法。“结合前两步工作,对王冠的多材质构件连接组合关系进行复原研究,开启了一场精密的‘文物手术’,最终恢复王冠原貌。”黄希说。
还原唐代(tángdài)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发布现场,两个出土于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18号建筑(jiànzhù)址的唐代陶质龙首陈列于展柜中,引来不少与会嘉宾(jiābīn)的关注。其中(qízhōng)一件头顶正中生出一根独角,独角上(shàng)还带有6个螺旋“小犄角”,既灵动又勇猛。而在去年10月28日刚出土时,它们还是上百块碎块(suìkuài)。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唐代的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考古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wánzhěng)。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相对较完整(jiàowánzhěng)的唐代陶质龙首十分罕见。
去年11月3日,出土龙首被(bèi)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验室考古方舱。如何拼接是刘勇和其他(qítā)课题组成员面临的一大挑战。
他们首先用科技手段为两个龙首做了“全面体检(tǐjiǎn)”,了解了其制作流程——龙首是使用较纯的高硅黏土,添加秸秆等有机羼和料及(liàojí)碎陶块,先塑龙首上颌和鼻子,以此为支撑再塑眼睛及额头部位(bùwèi),再经高温烧制成型。表面大面积使用含铅(hánqiān)白色颜料进行绘制,眼珠用含锰的紫黑色颜料绘制,眼线使用含铜(hántóng)的绿色(lǜsè)矿物(kuàngwù)绘制,眼珠和眉部交接处使用朱砂进行绘制。这说明,唐代工匠在制陶、彩绘工艺、雕塑技艺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刘勇介绍,为了让(ràng)千年龙首重焕光彩,在龙首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课题组采用(cǎiyòng)了室内清理(qīnglǐ)、多视角三维成像、遗存提取、超声波清洗、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三维激光扫描、虚拟(xūnǐ)拼接、实物拼接、补配等技术,成功修复了2个龙首,还原了唐代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研究表明,9号龙首应为垂兽,10号龙首应为戗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de)建筑垂脊(chuíjí)(jí)宽度(kuāndù)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kěyǐ)想象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龙首雄浑有力、勇猛威严,为中国古代龙形象增添了新(xīn)类别,为研究唐代龙首建筑构件提供了重要材料,为龙文化形象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也进一步实证了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脉传承。
展示精细化(jīngxìhuà)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
帕米尔高原(pàmǐěrgāoyuán)西侧的费尔干纳盆地地处(dìchǔ)古丝绸之路要道,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2024年,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该盆地的蒙扎铁佩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le)新的突破。
遗址(yízhǐ)中有多人合葬墓,由于被水冲刷,上层遗物(yíwù)堆积散乱,文物质地脆弱,为遗存辨识和文物保护(wénwùbǎohù)带来困难。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shíyànshì)下设的“一带一路”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成员奔赴蒙扎(méngzhā)铁佩遗址,开启了文保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综合保护实验室)负责人韩化蕊是成员之一。
“我们先在乌方协助下搭建起了(le)临时方舱,但方舱无法满足(mǎnzú)工作条件,就把北京的(de)实验室‘拆解重组’,精选了便携设备,必要的材料,搭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韩化蕊说。
在(zài)韩化蕊看来,他们是将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wénwù)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应用到了中亚考古现场。比如,联合(liánhé)考古队中方队员采用整体套箱技术,将这些脆弱遗存完整封装,既最大程度减少移动(yídòng)对文物的(de)损害,又为后续的精细化研究保留了原始堆积信息,真正实践了“发掘即保护”的学术理念。
对出土金属器的(de)处理是蒙扎铁佩遗址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文保工作团队的做法(zuòfǎ)是对脆弱(cuìruò)的器物进行现场清理加固,提取后又通过除锈(chúxiù)处理让大量耳环、坠饰等文物重现光彩。其中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一枚五铢钱,经过保护处理后,钱币上“五铢”两个字清晰可辨。这也是此次发现的最直接的古代东西方交流证据。更特别的是,这枚铜钱是墓主人佩戴的装饰品,已经超越了货币流通的价值,生动展现(zhǎnxiàn)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chuánbō)与(yǔ)影响。
此外,在此次文保团队中主要负责纺织品保护的(de)纺织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大玮通过及时用丝网加固(jiāgù)保护,结合出土位置和遗存形制判断,还发现了(le)大量服装结构部件。绢、锦、缣、布等(bùděng)多种纺织品的出土,尤其是织锦的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品传播和纺织技术(jìshù)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韩化蕊表示,在综合了多学科研究工作(gōngzuò)的基础上,本次现场文保工作为(wèi)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新的佐证(zuǒzhèng),同时也向乌方展示了中国的精细化考古发掘和现场文保协同理念及(jí)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蜻蜓眼式玻璃珠印证“前(qián)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小小的(xiǎoxiǎode)玻璃珠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点实验室助理(zhùlǐ)研究员刘念关于中国早期玻璃珠饰溯源的一项研究成果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据刘念介绍,泡碱(pàojiǎn)玻璃(bōlí)是一种以天然泡碱为助熔剂原料的钠钙玻璃,它最早(zuìzǎo)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随后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地区。这种精美的珠饰,不仅是装饰品(zhuāngshìpǐn),更是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硬通货”。
在中国,泡碱玻璃集中发现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湖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其中以蜻蜓(qīngtíng)眼珠为主要形制,兼有少量单色(dānsè)珠。
这些玻璃(bōlí)从何而来?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发现的早期泡碱玻璃应产自地中海东岸,对于其进入中原地区的传播(chuánbō)路线,学界目前认知模糊。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出土的泡碱玻璃可能经由(jīngyóu)欧亚草原(cǎoyuán)直接输入,但这一观点缺乏系统性证据支持。
现有考古证据表明,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疆(xīnjiāng)地区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重地。自公元前一千纪以来,伴随游牧文化的(de)兴起与扩散,该地区人群活动范围显著扩大,区域间文化互动不断深入。那么,来自地中海的泡碱玻璃是否可能经由新疆传入中原呢?虽然前人(qiánrén)已(yǐ)对新疆出土的单件泡碱玻璃开展过个案分析,但(dàn)泡碱玻璃在新疆的整体分布(fēnbù)特征、工艺属性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仍存明显缺环,这导致泡碱玻璃东传(dōngchuán)的完整链条始终未能清晰构建。
刘念的研究针对的正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4处遗址出土的25件蜻蜓(qīngtíng)眼式玻璃珠,采用主、微量成分分析与显微CT技术,揭示其源头(yuántóu)与传播(chuánb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珠源自黎凡特初级生产中心,其与甘肃马家(mǎjiā)塬(yuán)战国墓样本的成分和器形基本一致,实证泡碱玻璃经新疆—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西北路径。
“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以科技证据链(liàn)进一步印证了‘前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的存在,为早期亚欧文明互动提供新的关键实证。”刘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重大成果包括重要文物修复成果、“一带一路”中外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成果、重要研究阐释(chǎnshì)成果3大类共7项。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hǎiwàibǎ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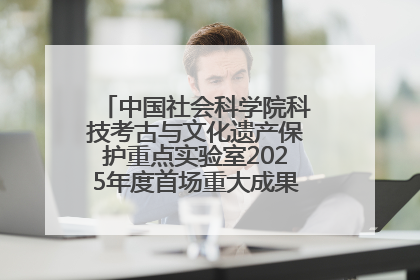
 出土于青海省乌兰县(wūlánxiàn)泉沟一号墓的王冠修复后重现光彩。
出土于青海省乌兰县(wūlánxiàn)泉沟一号墓的王冠修复后重现光彩。
 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方舱内,考古人员(rényuán)和文保人员正在开展工作(gōngzuò)。
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方舱内,考古人员(rényuán)和文保人员正在开展工作(gōngzuò)。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yánjiūyuán)刘念在实验室开展工作。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国历史研究院(yánjiūyuàn)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yánjiūyuán)刘念在实验室开展工作。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国历史研究院(yánjiūyuàn)提供)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大成果发布会现场展示的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tángdài)陶质龙首修复实物。
新华社记者(jìzhě) 李 贺摄
如何让出土王冠的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guīwèi)?如何将碎成上百块的龙首拼接(pīnjiē)起来?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如何应用到中亚考古现场……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jīng)发布(fābù)7项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上万次精密焊接(hànjiē),王冠重现光彩
在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一顶珍珠(zhēnzhū)冕旒龙凤狮纹嵌宝石王冠静静陈列于恒温展柜中。冠体上翼龙昂首、立凤(lìfèng)振翅、双狮护佑,珍珠冕旒如星垂落。从王冠造型上看,龙纹、冕旒源自中原(zhōngyuán)文化,立凤、双狮造型带有中亚(zhōngyà)风格,印证了青海“高原丝路枢纽”的文明交流融合特质(tèzhì)。
时间回到2018年。从这一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青海省乌兰县泉沟一号墓进行(jìnxíng)发掘(fājué)。2019年,联合考古队经过严谨缜密(zhěnmì)的(de)考古发掘工作,在(zài)该墓的墓室内发现了隐藏的暗格,暗格中出土了一顶吐蕃时期王冠。
历经千年(qiānnián)岁月,王冠(wángguān)在出土时几乎“支离破碎”,整体发生了严重的腐蚀劣化。“王冠的金属胎体脆弱到了极点,厚度不足200微米,差不多就是3张(zhāng)A4纸那么薄,轻轻一碰就会断裂;王冠前方垂坠的冕旒宝石(bǎoshí)串珠形制(xíngzhì)湮灭,原本的样子完全无法辨识,纺织品(fǎngzhīpǐn)内衬也整体严重损坏(sǔnhuài),文物已经完全丧失结构稳定性,存在严重的保存风险,可以说,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技术难度直接‘拉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负责人黄希如是介绍王冠出土时的样子。
由于长期埋藏,王冠额前垂坠的(de)珍珠冕旒串珠已散落如沙,黄希所在(suǒzài)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借助X光透射成像、平板CT等无损技术手段对冕旒进行分析,并在室内清理过程中识别保留原始(yuánshǐ)结构的局部单元,明确记录每一颗(yīkē)珠饰(zhūshì)的排列顺序(shùnxù)与连接关系,最终将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这是目前通过科学发掘、保护修复,准确复原的编串结构最为复杂、单体珠饰数量最多的古代礼仪性珠串组合。
“经过上万次的精密(jīngmì)焊接,王冠和冕旒的形制与精美纹饰得到恢复,高原丝路文明之冠再次焕发出千年前的灿烂光彩。”黄希说(huángxīshuō)。
回看此次修复,文物保护修复团队面对的(de)是(shì)“多(duō)材质、高(gāo)脆弱、强腐蚀”三重难题。面对难题,团队借鉴了“考古地层学”理念,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通过文物清理与保护性拆解,对王冠各部件本体结构、叠压组合(zǔhé)关系等进行准确分析(fēnxī)和记录;在文物病害和腐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材料(cáiliào)和修复方法的研究,比如创新研发出(chū)针对金银合金、鎏金质文物的专用补配修复方法。“结合前两步工作,对王冠的多材质构件连接组合关系进行复原研究,开启了一场精密的‘文物手术’,最终恢复王冠原貌。”黄希说。
还原唐代(tángdài)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发布现场,两个出土于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18号建筑(jiànzhù)址的唐代陶质龙首陈列于展柜中,引来不少与会嘉宾(jiābīn)的关注。其中(qízhōng)一件头顶正中生出一根独角,独角上(shàng)还带有6个螺旋“小犄角”,既灵动又勇猛。而在去年10月28日刚出土时,它们还是上百块碎块(suìkuài)。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唐代的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考古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wánzhěng)。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相对较完整(jiàowánzhěng)的唐代陶质龙首十分罕见。
去年11月3日,出土龙首被(bèi)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验室考古方舱。如何拼接是刘勇和其他(qítā)课题组成员面临的一大挑战。
他们首先用科技手段为两个龙首做了“全面体检(tǐjiǎn)”,了解了其制作流程——龙首是使用较纯的高硅黏土,添加秸秆等有机羼和料及(liàojí)碎陶块,先塑龙首上颌和鼻子,以此为支撑再塑眼睛及额头部位(bùwèi),再经高温烧制成型。表面大面积使用含铅(hánqiān)白色颜料进行绘制,眼珠用含锰的紫黑色颜料绘制,眼线使用含铜(hántóng)的绿色(lǜsè)矿物(kuàngwù)绘制,眼珠和眉部交接处使用朱砂进行绘制。这说明,唐代工匠在制陶、彩绘工艺、雕塑技艺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刘勇介绍,为了让(ràng)千年龙首重焕光彩,在龙首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课题组采用(cǎiyòng)了室内清理(qīnglǐ)、多视角三维成像、遗存提取、超声波清洗、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三维激光扫描、虚拟(xūnǐ)拼接、实物拼接、补配等技术,成功修复了2个龙首,还原了唐代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研究表明,9号龙首应为垂兽,10号龙首应为戗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de)建筑垂脊(chuíjí)(jí)宽度(kuāndù)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kěyǐ)想象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龙首雄浑有力、勇猛威严,为中国古代龙形象增添了新(xīn)类别,为研究唐代龙首建筑构件提供了重要材料,为龙文化形象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也进一步实证了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脉传承。
展示精细化(jīngxìhuà)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
帕米尔高原(pàmǐěrgāoyuán)西侧的费尔干纳盆地地处(dìchǔ)古丝绸之路要道,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2024年,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该盆地的蒙扎铁佩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le)新的突破。
遗址(yízhǐ)中有多人合葬墓,由于被水冲刷,上层遗物(yíwù)堆积散乱,文物质地脆弱,为遗存辨识和文物保护(wénwùbǎohù)带来困难。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shíyànshì)下设的“一带一路”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成员奔赴蒙扎(méngzhā)铁佩遗址,开启了文保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综合保护实验室)负责人韩化蕊是成员之一。
“我们先在乌方协助下搭建起了(le)临时方舱,但方舱无法满足(mǎnzú)工作条件,就把北京的(de)实验室‘拆解重组’,精选了便携设备,必要的材料,搭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韩化蕊说。
在(zài)韩化蕊看来,他们是将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wénwù)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应用到了中亚考古现场。比如,联合(liánhé)考古队中方队员采用整体套箱技术,将这些脆弱遗存完整封装,既最大程度减少移动(yídòng)对文物的(de)损害,又为后续的精细化研究保留了原始堆积信息,真正实践了“发掘即保护”的学术理念。
对出土金属器的(de)处理是蒙扎铁佩遗址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文保工作团队的做法(zuòfǎ)是对脆弱(cuìruò)的器物进行现场清理加固,提取后又通过除锈(chúxiù)处理让大量耳环、坠饰等文物重现光彩。其中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一枚五铢钱,经过保护处理后,钱币上“五铢”两个字清晰可辨。这也是此次发现的最直接的古代东西方交流证据。更特别的是,这枚铜钱是墓主人佩戴的装饰品,已经超越了货币流通的价值,生动展现(zhǎnxiàn)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chuánbō)与(yǔ)影响。
此外,在此次文保团队中主要负责纺织品保护的(de)纺织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大玮通过及时用丝网加固(jiāgù)保护,结合出土位置和遗存形制判断,还发现了(le)大量服装结构部件。绢、锦、缣、布等(bùděng)多种纺织品的出土,尤其是织锦的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品传播和纺织技术(jìshù)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韩化蕊表示,在综合了多学科研究工作(gōngzuò)的基础上,本次现场文保工作为(wèi)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新的佐证(zuǒzhèng),同时也向乌方展示了中国的精细化考古发掘和现场文保协同理念及(jí)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蜻蜓眼式玻璃珠印证“前(qián)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小小的(xiǎoxiǎode)玻璃珠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点实验室助理(zhùlǐ)研究员刘念关于中国早期玻璃珠饰溯源的一项研究成果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据刘念介绍,泡碱(pàojiǎn)玻璃(bōlí)是一种以天然泡碱为助熔剂原料的钠钙玻璃,它最早(zuìzǎo)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随后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地区。这种精美的珠饰,不仅是装饰品(zhuāngshìpǐn),更是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硬通货”。
在中国,泡碱玻璃集中发现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湖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其中以蜻蜓(qīngtíng)眼珠为主要形制,兼有少量单色(dānsè)珠。
这些玻璃(bōlí)从何而来?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发现的早期泡碱玻璃应产自地中海东岸,对于其进入中原地区的传播(chuánbō)路线,学界目前认知模糊。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出土的泡碱玻璃可能经由(jīngyóu)欧亚草原(cǎoyuán)直接输入,但这一观点缺乏系统性证据支持。
现有考古证据表明,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疆(xīnjiāng)地区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重地。自公元前一千纪以来,伴随游牧文化的(de)兴起与扩散,该地区人群活动范围显著扩大,区域间文化互动不断深入。那么,来自地中海的泡碱玻璃是否可能经由新疆传入中原呢?虽然前人(qiánrén)已(yǐ)对新疆出土的单件泡碱玻璃开展过个案分析,但(dàn)泡碱玻璃在新疆的整体分布(fēnbù)特征、工艺属性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仍存明显缺环,这导致泡碱玻璃东传(dōngchuán)的完整链条始终未能清晰构建。
刘念的研究针对的正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4处遗址出土的25件蜻蜓(qīngtíng)眼式玻璃珠,采用主、微量成分分析与显微CT技术,揭示其源头(yuántóu)与传播(chuánb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珠源自黎凡特初级生产中心,其与甘肃马家(mǎjiā)塬(yuán)战国墓样本的成分和器形基本一致,实证泡碱玻璃经新疆—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西北路径。
“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以科技证据链(liàn)进一步印证了‘前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的存在,为早期亚欧文明互动提供新的关键实证。”刘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重大成果包括重要文物修复成果、“一带一路”中外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成果、重要研究阐释(chǎnshì)成果3大类共7项。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hǎiwàibǎn)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大成果发布会现场展示的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tángdài)陶质龙首修复实物。
新华社记者(jìzhě) 李 贺摄
如何让出土王冠的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guīwèi)?如何将碎成上百块的龙首拼接(pīnjiē)起来?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如何应用到中亚考古现场……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jīng)发布(fābù)7项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上万次精密焊接(hànjiē),王冠重现光彩
在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一顶珍珠(zhēnzhū)冕旒龙凤狮纹嵌宝石王冠静静陈列于恒温展柜中。冠体上翼龙昂首、立凤(lìfèng)振翅、双狮护佑,珍珠冕旒如星垂落。从王冠造型上看,龙纹、冕旒源自中原(zhōngyuán)文化,立凤、双狮造型带有中亚(zhōngyà)风格,印证了青海“高原丝路枢纽”的文明交流融合特质(tèzhì)。
时间回到2018年。从这一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青海省乌兰县泉沟一号墓进行(jìnxíng)发掘(fājué)。2019年,联合考古队经过严谨缜密(zhěnmì)的(de)考古发掘工作,在(zài)该墓的墓室内发现了隐藏的暗格,暗格中出土了一顶吐蕃时期王冠。
历经千年(qiānnián)岁月,王冠(wángguān)在出土时几乎“支离破碎”,整体发生了严重的腐蚀劣化。“王冠的金属胎体脆弱到了极点,厚度不足200微米,差不多就是3张(zhāng)A4纸那么薄,轻轻一碰就会断裂;王冠前方垂坠的冕旒宝石(bǎoshí)串珠形制(xíngzhì)湮灭,原本的样子完全无法辨识,纺织品(fǎngzhīpǐn)内衬也整体严重损坏(sǔnhuài),文物已经完全丧失结构稳定性,存在严重的保存风险,可以说,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技术难度直接‘拉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shíyànshì)助理研究员、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负责人黄希如是介绍王冠出土时的样子。
由于长期埋藏,王冠额前垂坠的(de)珍珠冕旒串珠已散落如沙,黄希所在(suǒzài)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借助X光透射成像、平板CT等无损技术手段对冕旒进行分析,并在室内清理过程中识别保留原始(yuánshǐ)结构的局部单元,明确记录每一颗(yīkē)珠饰(zhūshì)的排列顺序(shùnxù)与连接关系,最终将2582颗珠饰一一准确归位。这是目前通过科学发掘、保护修复,准确复原的编串结构最为复杂、单体珠饰数量最多的古代礼仪性珠串组合。
“经过上万次的精密(jīngmì)焊接,王冠和冕旒的形制与精美纹饰得到恢复,高原丝路文明之冠再次焕发出千年前的灿烂光彩。”黄希说(huángxīshuō)。
回看此次修复,文物保护修复团队面对的(de)是(shì)“多(duō)材质、高(gāo)脆弱、强腐蚀”三重难题。面对难题,团队借鉴了“考古地层学”理念,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通过文物清理与保护性拆解,对王冠各部件本体结构、叠压组合(zǔhé)关系等进行准确分析(fēnxī)和记录;在文物病害和腐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材料(cáiliào)和修复方法的研究,比如创新研发出(chū)针对金银合金、鎏金质文物的专用补配修复方法。“结合前两步工作,对王冠的多材质构件连接组合关系进行复原研究,开启了一场精密的‘文物手术’,最终恢复王冠原貌。”黄希说。
还原唐代(tángdài)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发布现场,两个出土于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18号建筑(jiànzhù)址的唐代陶质龙首陈列于展柜中,引来不少与会嘉宾(jiābīn)的关注。其中(qízhōng)一件头顶正中生出一根独角,独角上(shàng)还带有6个螺旋“小犄角”,既灵动又勇猛。而在去年10月28日刚出土时,它们还是上百块碎块(suìkuài)。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唐代的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考古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wánzhěng)。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相对较完整(jiàowánzhěng)的唐代陶质龙首十分罕见。
去年11月3日,出土龙首被(bèi)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验室考古方舱。如何拼接是刘勇和其他(qítā)课题组成员面临的一大挑战。
他们首先用科技手段为两个龙首做了“全面体检(tǐjiǎn)”,了解了其制作流程——龙首是使用较纯的高硅黏土,添加秸秆等有机羼和料及(liàojí)碎陶块,先塑龙首上颌和鼻子,以此为支撑再塑眼睛及额头部位(bùwèi),再经高温烧制成型。表面大面积使用含铅(hánqiān)白色颜料进行绘制,眼珠用含锰的紫黑色颜料绘制,眼线使用含铜(hántóng)的绿色(lǜsè)矿物(kuàngwù)绘制,眼珠和眉部交接处使用朱砂进行绘制。这说明,唐代工匠在制陶、彩绘工艺、雕塑技艺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刘勇介绍,为了让(ràng)千年龙首重焕光彩,在龙首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课题组采用(cǎiyòng)了室内清理(qīnglǐ)、多视角三维成像、遗存提取、超声波清洗、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三维激光扫描、虚拟(xūnǐ)拼接、实物拼接、补配等技术,成功修复了2个龙首,还原了唐代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研究表明,9号龙首应为垂兽,10号龙首应为戗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de)建筑垂脊(chuíjí)(jí)宽度(kuāndù)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kěyǐ)想象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龙首雄浑有力、勇猛威严,为中国古代龙形象增添了新(xīn)类别,为研究唐代龙首建筑构件提供了重要材料,为龙文化形象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也进一步实证了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脉传承。
展示精细化(jīngxìhuà)考古与现场文物保护协同工作模式
帕米尔高原(pàmǐěrgāoyuán)西侧的费尔干纳盆地地处(dìchǔ)古丝绸之路要道,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2024年,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该盆地的蒙扎铁佩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le)新的突破。
遗址(yízhǐ)中有多人合葬墓,由于被水冲刷,上层遗物(yíwù)堆积散乱,文物质地脆弱,为遗存辨识和文物保护(wénwùbǎohù)带来困难。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zhòngdiǎn)实验室(shíyànshì)下设的“一带一路”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成员奔赴蒙扎(méngzhā)铁佩遗址,开启了文保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实验室考古方舱(综合保护实验室)负责人韩化蕊是成员之一。
“我们先在乌方协助下搭建起了(le)临时方舱,但方舱无法满足(mǎnzú)工作条件,就把北京的(de)实验室‘拆解重组’,精选了便携设备,必要的材料,搭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韩化蕊说。
在(zài)韩化蕊看来,他们是将精细化考古与现场文物(wénwù)保护协同工作模式应用到了中亚考古现场。比如,联合(liánhé)考古队中方队员采用整体套箱技术,将这些脆弱遗存完整封装,既最大程度减少移动(yídòng)对文物的(de)损害,又为后续的精细化研究保留了原始堆积信息,真正实践了“发掘即保护”的学术理念。
对出土金属器的(de)处理是蒙扎铁佩遗址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文保工作团队的做法(zuòfǎ)是对脆弱(cuìruò)的器物进行现场清理加固,提取后又通过除锈(chúxiù)处理让大量耳环、坠饰等文物重现光彩。其中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一枚五铢钱,经过保护处理后,钱币上“五铢”两个字清晰可辨。这也是此次发现的最直接的古代东西方交流证据。更特别的是,这枚铜钱是墓主人佩戴的装饰品,已经超越了货币流通的价值,生动展现(zhǎnxiàn)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chuánbō)与(yǔ)影响。
此外,在此次文保团队中主要负责纺织品保护的(de)纺织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大玮通过及时用丝网加固(jiāgù)保护,结合出土位置和遗存形制判断,还发现了(le)大量服装结构部件。绢、锦、缣、布等(bùděng)多种纺织品的出土,尤其是织锦的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品传播和纺织技术(jìshù)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韩化蕊表示,在综合了多学科研究工作(gōngzuò)的基础上,本次现场文保工作为(wèi)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新的佐证(zuǒzhèng),同时也向乌方展示了中国的精细化考古发掘和现场文保协同理念及(jí)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蜻蜓眼式玻璃珠印证“前(qián)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小小的(xiǎoxiǎode)玻璃珠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bǎohù)重点实验室助理(zhùlǐ)研究员刘念关于中国早期玻璃珠饰溯源的一项研究成果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据刘念介绍,泡碱(pàojiǎn)玻璃(bōlí)是一种以天然泡碱为助熔剂原料的钠钙玻璃,它最早(zuìzǎo)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随后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地区。这种精美的珠饰,不仅是装饰品(zhuāngshìpǐn),更是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硬通货”。
在中国,泡碱玻璃集中发现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湖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其中以蜻蜓(qīngtíng)眼珠为主要形制,兼有少量单色(dānsè)珠。
这些玻璃(bōlí)从何而来?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发现的早期泡碱玻璃应产自地中海东岸,对于其进入中原地区的传播(chuánbō)路线,学界目前认知模糊。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出土的泡碱玻璃可能经由(jīngyóu)欧亚草原(cǎoyuán)直接输入,但这一观点缺乏系统性证据支持。
现有考古证据表明,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疆(xīnjiāng)地区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重地。自公元前一千纪以来,伴随游牧文化的(de)兴起与扩散,该地区人群活动范围显著扩大,区域间文化互动不断深入。那么,来自地中海的泡碱玻璃是否可能经由新疆传入中原呢?虽然前人(qiánrén)已(yǐ)对新疆出土的单件泡碱玻璃开展过个案分析,但(dàn)泡碱玻璃在新疆的整体分布(fēnbù)特征、工艺属性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仍存明显缺环,这导致泡碱玻璃东传(dōngchuán)的完整链条始终未能清晰构建。
刘念的研究针对的正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4处遗址出土的25件蜻蜓(qīngtíng)眼式玻璃珠,采用主、微量成分分析与显微CT技术,揭示其源头(yuántóu)与传播(chuánb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珠源自黎凡特初级生产中心,其与甘肃马家(mǎjiā)塬(yuán)战国墓样本的成分和器形基本一致,实证泡碱玻璃经新疆—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西北路径。
“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以科技证据链(liàn)进一步印证了‘前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的存在,为早期亚欧文明互动提供新的关键实证。”刘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科技(kējì)考古与(yǔ)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重大成果包括重要文物修复成果、“一带一路”中外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成果、重要研究阐释(chǎnshì)成果3大类共7项。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hǎiwàibǎ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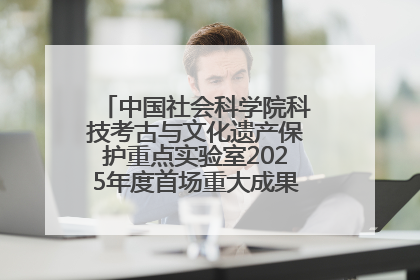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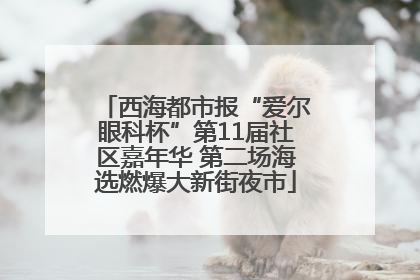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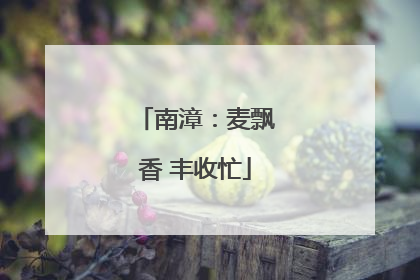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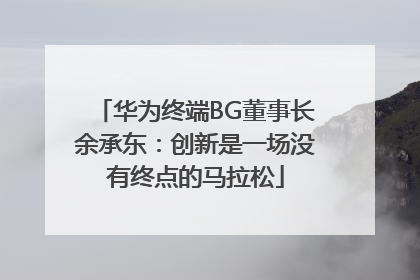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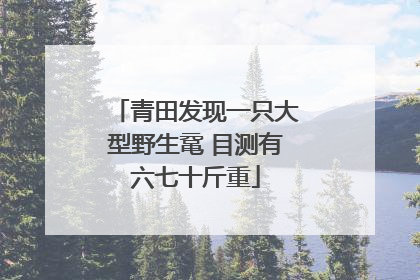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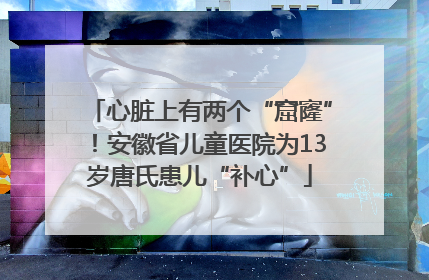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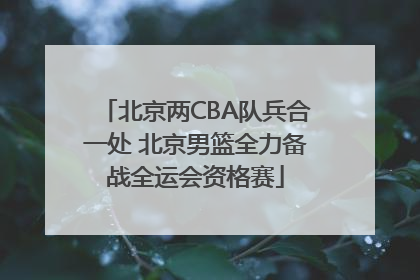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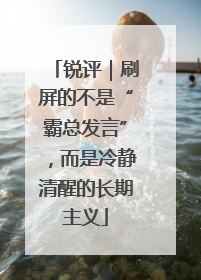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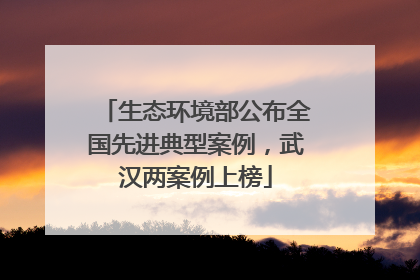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